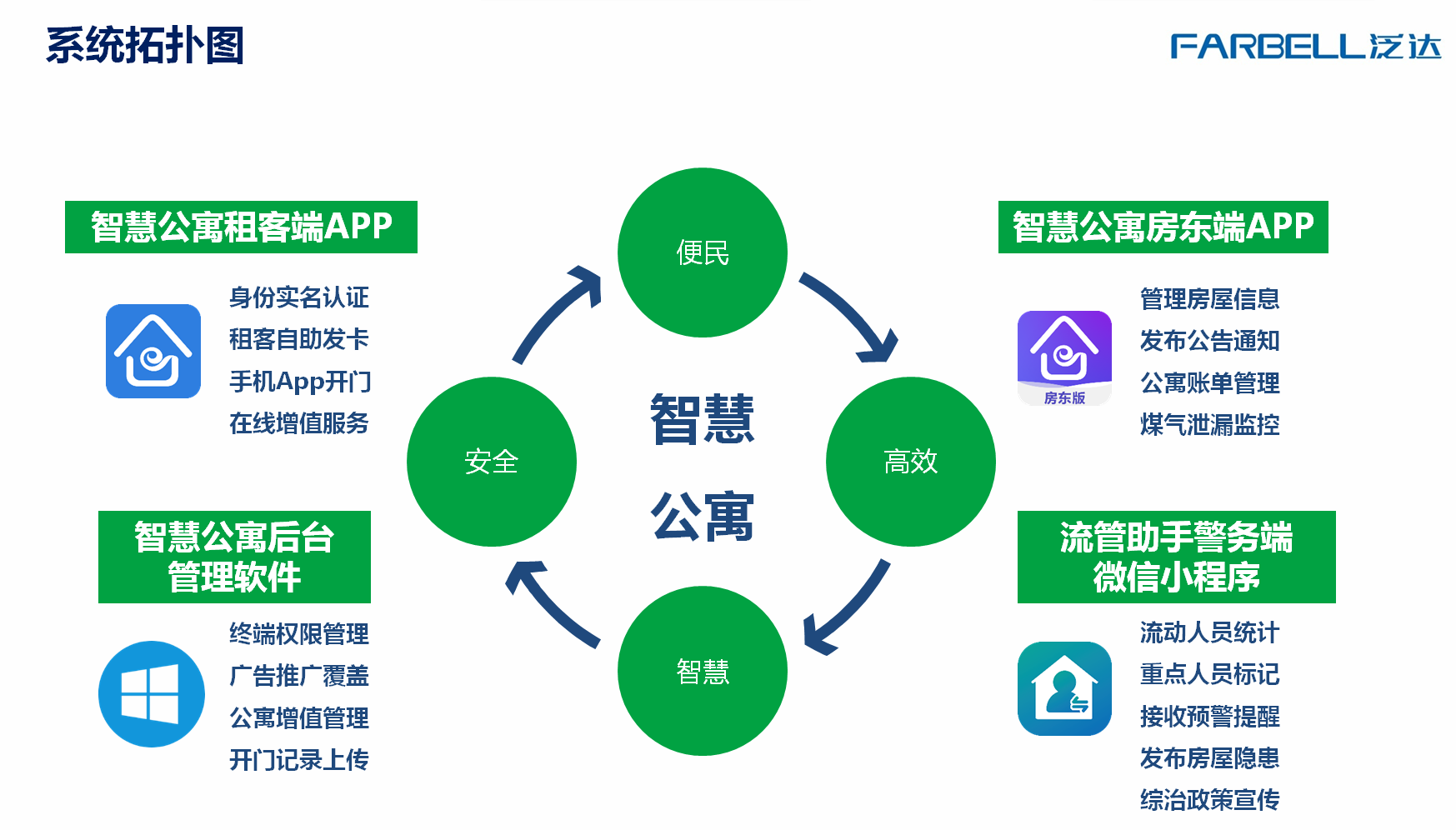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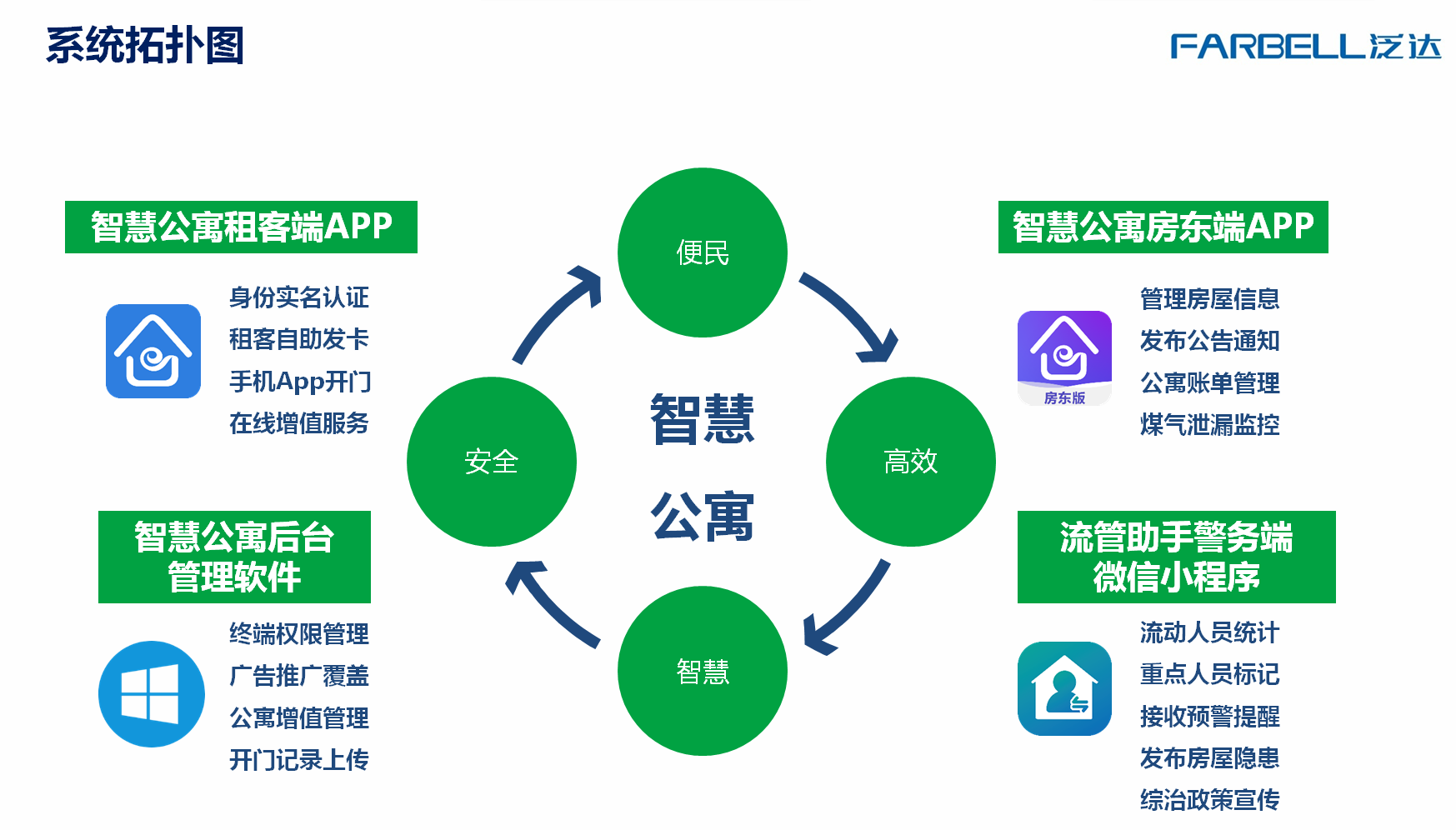
工厂里■■,大大小小的苦痛被加诸人身上,让人产生了被奴役的感觉。正如朱尔·罗曼斯所说:“这些细小的身体伤痛,劳动不需要也不会从中获益。”这些痛苦并非工作所必需;承担工作所需的痛苦会让人感到自豪,但工厂造成的痛苦却没有任何作用。它们会伤害灵魂◆■★■,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想对此抱怨;而且人们知道自己不会去想。
一份工作越能带来这样的困难■■★,就越能振奋人心。但如果没有能评价和欣赏我们成功价值的人,工友或老板■◆★■■,这份喜悦就是不完整的。无论领导或是负责同一零件其他操作的工友◆★★★■,大都只关心零件■★■◆■,而不关心所要克服的困难。这种冷漠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消散,而这份温情却是人们永远需要的◆★★◆。即使是最无所谓自尊心的人■★◆★★■,在一个人们只关心他所做的事情,而从不关心他是如何去做的地方也会感到特别的孤独;因此,工作的乐趣沦为一些转瞬即逝、未表明的印象,一出现就消失了。
在这样的痛苦面前,我们在肉体和思想上都退缩了。就好像有人在你耳边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而你却什么都不能说:“你在这里什么都不是。你不重要★◆。你在这里就是要服从,承受一切并保持沉默。◆■◆■”这样重复几乎无法抵抗。你开始在心底里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几乎所有的工厂工人,即使是那些表面看起来最独立的■■◆◆★,从他们的动作、眼神,尤其是嘴唇的皱褶中,也流露出某些很难察觉的东西,表现出他们被迫承认自己不重要。
人们多么希望能暂时寄存自己的灵魂,就带着计时卡进入工厂■★■◆★,在离开时再将灵魂原封不动地取回■◆◆■◆◆!但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带进工厂,让它在那里受苦;到了晚上,疲惫已将灵魂消磨殆尽,闲暇时光只剩虚无■★◆◆■◆。
当然,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偶然依然存在,只是不被承认。被认可的往往会对生产造成极大伤害,那是一种军营的规则:“我不想知道■◆■◆■■。”想象的力量在工厂是非常强大的。有些规则从未被遵守,却一直有效■◆◆★■◆。依据工厂的逻辑◆◆■,矛盾的命令无效。通过所有这一切◆★★,工作必须完成。让工人去处理,否则就解雇他。他自己去处理。
正如她自己所说,社会的不公早使她深受触动★★,是本能将她推向了贫苦大众一边。她的生命因这一永恒的选择具有了统一性。
人们在这嘈杂声中迷失,但同时又主宰着它,因为在这一贯持续■■、不断变化的低音中■★◆,显得突出又与其他声音相融合的是运行中的机器的声音。我们不像在人群中时那样感觉渺小,我们感到自己不可或缺。传送带——如果有的话——能让人们借由眼睛感知节奏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性通过声音和万物的轻微震动为我们整个身体所感知。
无论是处于21世纪的我们,还是上世纪30年代的■◆★★■■“打工人”,西蒙娜·薇依用一句话连结了我们的痛楚,即“工厂造成的痛苦没有任何作用■★。它们会伤害灵魂◆■”。
通常,当我们需要别人,一个工头■◆、仓库管理员或校准员,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那种需要依赖他人的无力感,以及在自己所依赖的人眼中一无是处的感觉,令我们感到如此痛苦,以致为此流泪■★■。如机器停转◆■、箱子消失等这类事件持续发生的可能性非但不能减轻工作单调的影响,反而让它丧失了自带的补救措施,即让思想沉寂■■■★■★,在某种程度上暂停感知的力量;轻微焦虑会阻碍这一暂停的效果◆■◆◆,迫使人感受单调■◆■■■,尽管这很难忍受★■★■★。
没有什么比单调和偶然搅在一起更糟糕的了;它们会让彼此情况恶化,至少当偶然性引起不安时是这样■◆■。工厂的单调令人不安◆★★◆★◆,因为其本身没有被承认◆★■★;理论上,尽管所有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存放加工好零件的箱子从未变少,校准工从来没让人等过,一切生产的延迟都是工人造成的。思想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既要关注不断重复同样动作的单调过程■◆★◆,又要从自身找方法应对突发状况。一份矛盾的、不可能达成且累人的责任◆◆。
当一个人工作时,能将自己所处的那一刻与手头零件的完工——如果幸运的话★◆,思想延续的时间能足够长到零件完工——区分开。这就是思想唯一可以承受的未来。超越这一界限,思想将无法向外拓展。在某些时刻■◆◆,你全神贯注地工作,思想因而得以保持在这些界限内。这样你就不会受苦。
主要是他们接受命令的方式逼迫他们如此◆★◆。人们常常否认工人受单调的工作所苦,因为他们注意到生产的变化对工人而言往往是一种困扰。然而,长期从事一项单调的工作★★◆■■◆,厌恶感会侵入灵魂。变化缓解痛苦的同时,也会造成困扰;在计件工作中,有时工人会感到非常气恼,一方面是由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工作期间★■◆◆,无法表达又难以捉摸的从属感已成为一种习惯,或几乎是一种惯例◆■■,它控制了人的灵魂◆★■。然而,即便工作是按小时支付,也会令人感到气恼■■★◆、烦躁■◆,因为工人是被命令做出改变的。
但晚上离开后★★■,或尤其是早上你走向工作地点和打卡钟的时候★★,一想到即将度过的一天★◆■◆■★,你就会感到非常痛苦★◆■。而到了周日晚上,你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不是一天,而是一整个星期时,就会觉得未来太过枯燥、压抑,思想也因此退缩了。
据官方声明,法国将设法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不复出现,即排除无论工厂内外■★★,工人生活中一切有损人格的东西◆■◆◆。第一个要克服的困难是无知。近年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厂工人其实是背井离乡、流浪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工厂可以用强烈的集体生活感——也可称之为一致生活感,工人因参与大型工厂工作获得这一感受——填充灵魂■■◆。所有的声音都有意义,一切都有节奏,它们融合在一种共同工作的伟大气息之中。参与其中令人陶醉,尤其是因为孤独的感觉没有改变◆■。只有金属的声音,转动的车轮以及金属焊接;这些声音不是自然或生命的声音,而是人类严肃、持续◆◆★★、不间断地在物体上操作的声音■★◆◆。
如果不清楚一种恶的构成■◆■★■◆,又怎么去废除它呢★◆?以下的几行文字或许至少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来自与工厂生活的直接接触■◆★★。
如果你手头的零件还需两小时完成,你就不能想三小时后要做什么,否则你的思绪会发生转移,让你想到老板,进而不得不反复告诉自己,你是在听从指令;如果你每分钟做十个零件,那么接下来的五分钟也是如此。假设也许不会有任何命令突然下达★★■★,由于命令是唯一的多样性因素,想要通过思考消除它,只不过是在想象自己不间断地重复做相同的零件。这如同一片沉闷又荒芜的沙漠◆★■◆◆★,是思想所无法穿越的。
因此◆◆★★★,工人们在谈及自身命运时,最常重复的却是那些并非他们创作的宣传词。就算是对已不再做工的人来说,困难也不小;对他而言,谈论他原先的生存状况很容易,但要确实地去思考却很难,因为没有什么比过往的不幸更容易被遗忘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可以借助故事,发挥想象力★◆■◆★◆,从外部进行某种程度的猜测和描述;正如朱尔·罗曼斯在《善意的人们》中用一章来描写工厂生活★■◆★◆。但并没有很深入★◆。
工厂单调的一天即使没有被任何工作变动打断,也混杂着无数琐事,它们充斥着每一天■◆■■◆,不断创造新的故事;与工作的变化一样,这些琐事造成的伤害往往大于它们带来的安慰■◆。在计件工作中★◆■★★■,它们总是与工资降低挂钩,因此,人们都不希望见到它们。而往往它们本身就具有伤害性。遍布工作每一刻的焦虑感,担心自己速度不够快的焦虑感正聚集于此。
冬天早晨和晚上的黑暗时分■◆◆■,只有电灯亮着,所有的感官都沉浸在同一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自然,什么都不是无偿的■★◆,一切都在冲突之中★★◆■◆;冲突虽然艰苦★★,同时也带来了胜利,那是人与物的冲突。灯具◆★、传送带、声音、坚硬而冰冷的废铁,一切都将人转变成了工人。
某些事尽管会造成工资减少★★◆◆★■,但的确能让我们在工作中收获快乐。首先是那些能让我们感受到珍贵情谊的事◆★■■★,这种情况很少★◆■★■;还有那些自己摆脱困境的事。当我们想方设法、努力克服困难时■★◆,我们的灵魂被对未来的设想所占据,而这未来仅取决于我们自身。
接下来的几行文字反映了一段 1936 年以前的工厂生活经历◆★■。对于很多仅在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影响下才与工人有了直接接触的人来说,这些文字可能会让他们惊讶。工人的境况一直在变化;有时一年与一年不同■■◆★◆◆。1936 年之前的几年尽管受经济危机影响■◆,生活异常艰难与残酷,但比起随后如梦般的时期却更好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
他们早就知道自己被粗暴对待后会一言不发地忍耐。说话就是找骂。通常■■◆,工人如果无法忍受某件事情■■★,他宁愿保持沉默并辞职。这样的痛苦本身往往是很轻的■◆■◆。如果它们令人痛苦,那是因为每当我们感受到它们★★◆★★◆,而且是不断地感受到它们时★★★◆◆◆,我们会提醒自己是多么想要忘记,我们在工厂有多不自在◆◆★★■,也没有任何权利◆★■,只是作为机器和待加工零件之间的一个简单中介被接纳,如同一个异乡人◆★■■★★;这些伤害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第一个使人感觉被奴役的细节是打卡钟◆★■■。无论从家到工厂的路程远近,最重要的是要在机器设定的前一秒钟到达。无所谓是提前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到★■◆■◆■;事实上◆★■◆■,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不存在任何偶然因素。在工人的一天中,这是要遵守的第一条规则,它严苛地主宰着所有在机器旁度过的生命;在工厂,偶然不被允许出现■■★■■。
但在工厂却并非如此。从打卡进厂到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每一刻都在接受命令。如同一个惰性物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改变你的位置★★。
但人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走访郊区,看看那些悲伤、昏暗的卧室以及房屋和街道◆■,这对了解一个人在那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没有多大帮助。工人在工厂所遭遇的不幸甚至更加神秘了。他们自己几乎不会写■■、不会说★★◆★◆■,甚至不会就此思考,因为不幸所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令人丧失思考能力;受不幸所伤◆★,他们也不愿再对它进行思考■★◆■。
《工厂日记》可以被看作是一本真正的“日记”。这位身体瘦弱的法国哲学家通过真实地在工厂里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放下自我的意识、忍受机器的噪音、重复繁重的工作◆◆,她了解了这些工人的苦难,于是,她义愤填膺,但又带着某种渴望社会改变的心■◆◆■,写下了这些文字。
如果这就是工厂生活■★,那就太美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快乐属于自由的人;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因为不自由,除了短暂、罕见的瞬间,他们从未感受到快乐。他们只有忘记了自己的不自由才能感觉到快乐★★■◆■★;但他们却很少能忘记◆◆◆■,因为通过感官和身体,从遍布生命每一分钟的千万个小细节◆■◆★■,他们感受到的是作为下属的被束缚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晚上离开工厂时■◆■★★,身体有时会感到疲惫,而思想却是一直如此,且疲惫感更甚。任何有过这种感受且没有遗忘的人,几乎都能从晚上离开工厂的工人眼里读出这份疲惫。
事实上,在这片沙漠里的确会发生无数琐事■◆◆,如果它们在过去的一小时里是重要的,它们却不会出现在你所设想的未来◆■。你想用思考排遣单调,想象变化,即一个突然的命令,但却不得不经历屈辱才能让思想由当下抵达未来。于是,你的思想退缩了■★◆◆■★。这种当下的退缩导致了思想的僵化■★■◆★◆。
新的工作以命令的形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安排下来,工人们必须立即服从、不得辩驳。因而,服从命令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一直在受别人支配。拥有一个机械作坊的小工匠知道自己在两个星期内必须提供这么多的曲轴、阀门、连杆,他也不会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至少,一旦他接受了订单,就得事先决定好他的日程安排。如果老板提前一两个星期对工人说■★◆★■★:这两天你要制造连杆、曲轴等等,工人必须服从,但他可以在脑海中设想一下,提前规划好再去操作★★■★。